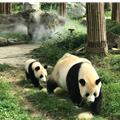自然教育和環境教育 到底有什么區別?
我被很多業內人士看作是環境教育(或者說自然教育)領域的“資深人士”,因此也經常被問及這個問題。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太在意,覺得這個問題沒什么好說的,誰愛用哪個就用哪個。后來發現問這個問題的人還很多,也確實困擾了不少對自然教育感興趣,并從事相關工作的人。既然我在這一領域工作較久,那確實該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和經歷,希望這對自然教育的從業者能夠有所啟發。
不過,事先要聲明的是,這不是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只是通過我的經歷和感悟,分享我對環境教育和自然教育的看法,這不是“權威”的論斷。文章中,我會涉及一些人和事,由于時間久遠,可能細節上有誤差,如果有什么疏漏,我愿意文責自負。
2006年到2008年,我在美國的環境教育重鎮——威斯康星大學斯蒂芬角校區攻讀環境教育及解說碩士。我之所以有機會去美國讀書,是因為獲得了福特獎學金的資助。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國際項目,我至今以入選這個獎學金為榮,并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自然教育領域,用以回報這個獎學金給予我的幫助。
但在我去美國讀書之前,并不知道還有個叫“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education)的專業。是獎學金面試官通過我的表述向我推薦的課程。后來我才意識到,雖然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環境教育”這個詞,但我與獎學金辦公室老師的對話,已經無意中談及了環境教育的核心定義——關注人行為的改變,這一點我會在下文詳細談到。
在這里我不想做環境教育的考據研究,也不想引用各種環境教育的經典定義。但有一件事確實值得關注環境教育的人知曉,那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環境規劃署1977年10月在第比利斯(現在的格魯吉亞首都,那時候屬蘇聯)召開了68個國家參加的政府間環境教育大會,會議發表了著名的《第比利斯宣言》,提到了環境教育的五大要素:意識(Awareness)、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技能(Skills)和參與(Participation)。也就是說,如果你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環境教育,就應該盡可能地考慮到以上這5個要素,這也是我們經常說的“僅僅告訴別人知識是不夠的”重要的理論依據,因為還要考慮其他4個要素呢!這也是為什么在上文中提到,即便我那時還不知道環境教育這個詞,但我已經在和福特獎學金辦公室老師的交流過程中,表露出了和環境教育一致的理解——要通過觀鳥活動去影響人、改變人。
還有一點值得說明的是,后來聯合國不太使用環境教育這個詞了,開始用可持續發展教育(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ESD),歐洲國家用的也不多,北美倒是一直在使用環境教育的表述方法,特別是在學術領域。
《林間最后的小孩》一書在中國出版后便得到迅速認可,書中提到的“自然缺失癥”也開始被公眾廣泛接受。
這時候,“自然教育”這個詞開始出現了。考證第一次出現“自然教育”一詞是什么時候已經沒有意義。但必須要提一件與此相關的重要事件。
2010年前后,一家叫中日公益伙伴的機構在國內組織了一系列的活動,介紹日本的自然學校。中日公益伙伴不僅在全國舉辦了多場介紹日本自然學校的交流分享,還組織國內自然教育的活躍分子去日本實地考察。2013年4月,我有幸被選中參加了為期一周的日本自然學校考察項目,收獲良多。
同年9月在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舉辦了中日自然學校網絡會議。會議請來了日本自然學校的高木晴光先生、梅崎靖志先生和森美文先生與大家進行交流。他們以自己創辦自然學校的經歷為切入點,介紹了日本自然學校網絡的建立歷史,分享了他們20多年來的經驗和感悟。隨后,這樣類型的交流會又在成都、北京等地舉辦了多次。中日公益伙伴策劃和執行的這些項目,為中國自然教育界培養了一群專業能力扎實的從業者,也為中國自然教育搭建起了早期的專業交流平臺。
我曾在一次采訪中說:“中日公益伙伴組織的中日自然學校交流項目是大陸較早地推動自然教育網絡建設的活動,具有奠基石的重要作用。參加第一次在西雙版納植物園舉行的自然學校網絡會議代表,很多都已經是當前大陸自然教育領域的活躍人物。當初能夠發起這個項目的人,都是具有長遠的眼光和情懷,必然在中國自然教育歷史上留下一筆。”我至今仍相信這個判斷。
我認為,《林間最后的小孩》出版和日本自然學校模式在國內的推廣,催生了“自然教育”這個詞在國內的出現和自然教育本身的發展。
實事求是地說,當“自然教育”這個詞開始出現的時候,我還是挺反對的。我當時認為,既然有了環境教育,為什么又要搞個自然教育出來呢?在我看來,兩者沒有什么大的差別呀,兩個詞很容易把人搞糊涂!
我對“兩個詞容易把人搞糊涂”的判斷基本沒有錯。但我對自然教育這個詞的使用態度后來卻轉變了,這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大家確實喜歡用“自然教育”這個詞,我反對也沒有什么用。既然如此,何必死抱住舊觀念不放呢?很明顯,在漢語的語境里,“自然”這個詞自帶美好的寓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鳥語花香、微風拂面等美好體驗,而“環境”則沒有這樣的效果。這也怪不得大家喜歡用“自然教育”。
其次,自然教育好像在某些方面確實和環境教育不一樣。比如,受眾年齡上,自然教育的受眾明顯是偏向8-12歲的小學生。雖然也有中學生和成人愿意接觸自然教育,但這不是當前自然教育的主要受眾人群。另外,自然教育確實沒有環境教育那樣高大的使命感。自然教育主要是鼓勵孩子們去戶外玩耍,多認識花花草草,雖然也會涉及尊重、友愛、合作等內容,但大家確實不太談改變人的行為這一層次。并且,自然教育雖然也鼓勵孩子們在周邊觀察自然,但現在以深度自然體驗為主要目的的長途旅行反而成了一個重要特色。
再次,我意識到,自然教育在中國的突然出現,肯定是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變化相關的。既然它有著自己產生的獨特歷史背景,為什么我一定要用一個幾十年前的詞匯去指代它呢?誰敢保證,這個在中國當前環境下產生的新事物,未來不會走出真正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來?說不定,隨著它的發展和成熟,有了自己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案例,自然教育還會成為中國對國際社會的一個貢獻呢!
我曾經也就這個問題去問臺灣的環境教育學者張子超先生。張老師微笑地看著我說:“西敏,你知道嗎,這兩個詞被發明出來,并不是為了讓你去區分它們。”我為如此睿智的回答而嘆服。
這樣的描述對你有幫助嗎?
| 我也說兩句 |
| E-File帳號:用戶名: 密碼: [注冊] |
| 評論:(內容不能超過500字。) |
*評論內容將在30分鐘以后顯示! |
| 版權聲明: 1.依據《服務條款》,本網頁發布的原創作品,版權歸發布者(即注冊用戶)所有;本網頁發布的轉載作品,由發布者按照互聯網精神進行分享,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無商業獲利行為,無版權糾紛。 2.本網頁是第三方信息存儲空間,阿酷公司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服務對象為注冊用戶。該項服務免費,阿酷公司不向注冊用戶收取任何費用。 名稱:阿酷(北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聯系人:李女士,QQ468780427 網絡地址:www.arkoo.com 3.本網頁參與各方的所有行為,完全遵守《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如有侵權行為,請權利人通知阿酷公司,阿酷公司將根據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刪除侵權作品。 |
 m.quanpro.cn
m.quanpro.cn